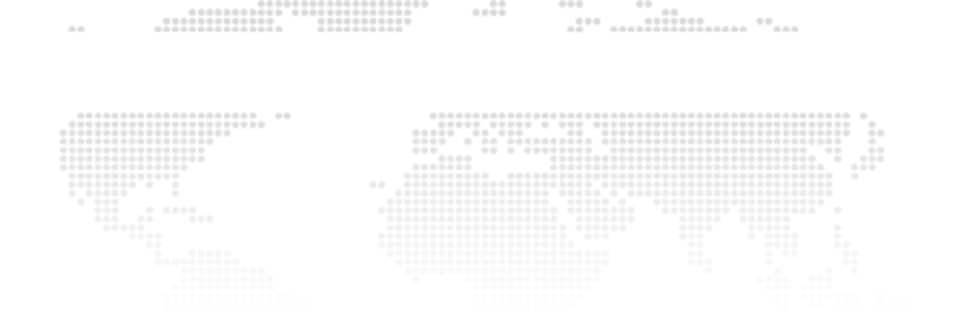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报告发布 ▏吴晓林:超大城市风险防控的脆弱性与行政区划
阅读量: 发布时间:2021-10-26
2021年9月29日下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晓林教授在“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做了题为《超大城市风险防控的脆弱性与行政区划》的精彩发言。
文/吴晓林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晓林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超大城市的发展情况。目前,我国有7座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18%,但却贡献了全国32.9%的GDP,未来随着一些新兴特大城市的出现以及现有特大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特大城市占全国GDP比重的预期还将继续上升,甚至未来可能占到50%以上。但人口规模与城市风险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研究表明,在大城市中,随着人口规模增加100%,犯罪率会增加120%,一项在广州的研究表明,不论是侵财犯罪风险还是把暴力犯罪风险,皆是旧城区最大,核心区最小。既有研究基本都是以空间规划和人口规模的调整作为风险的系统变量,以疏解人口和进行空间隔离作为控制风险的手段。
吴教授认为,现有研究仍有缺口,因为并不能通过空间的界线划分就能很好很好地应对城市风险,行政区划只是影响风险防控的一个系统变量,真正影响风险防控的是附着于区划之上的“脆弱性”(反面就是韧性),但是,相关研究缺乏风险防控与空间脆弱性的关联分析。中国城市对风险的防控基础是属地化管理,我国的最高层法律和具体法规确立了每个层级政府主体的责任,要求把乡镇、街道(到了基层则把村、社区)都纳入到风险防控体系中来,各负其责,进行属地化管理。
吴晓林教授探索归纳出属地化管理的三类脆弱性。第一类是行政区与管辖权不统一的风险。在特大城市中,有些地方甚至分不清街道办的具体管辖范围,各种原因造成的插花地的管理和责任归属则更加难以界定。另一方面,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功能区,和行政区划是重叠关系,当出现问题时便难以问责,2013年青岛油管爆炸和2015年天津港大爆炸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第二类是风险跨区域“溢出扩散”,既有属地管理无法应对。城市的风险灾害不是孤立事件,往往是以灾害链的形式出现,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管理,由于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单独靠一个行政区划来应对几乎不可能,我们对口支援和联动机制较好地缓解了这一点。第三类是区划规模太大,风险治理超载。在我国的特大城市中,建成区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数量超过一万,佛山的城市建成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承载的人口甚至超过六万,我国最大的街道办超过一百万人口,最大的小区达到五十多万人口,在此情形下,我国基层管理往往是一个管理人员对应一千人的社区服务,在具体的风险防控中承担了大量的职责。调研表明,目前社区在辖区内需要承担29项安全检查,但是社区缺乏对应的专业能力和行政手段。
针对属地管理在风险防控方面由物理特质和社会特质所带来的脆弱性,吴教授基于脆弱性的理论视角,提出了三区、三圈层韧性城市的路径。第一是在社区层面,基于人居安全需求推动安全场景营造,真正服务于人的需求。第二是在政区层面,基于人口密度和规模做好行政区划,避免中心城区或郊区过大,必要时推动行政区划从块状向扇形转变,以利于区划调整和优质资源向外扩散。第三是在跨区层面,基于安全风险的类型推动跨域治理,日常风险可以由行政区自行承担责任,例外风险就需要区域间的协同,诸如疫情这样的战略风险则需要跨区域协同。
(本文系嘉宾9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文稿整理:林晓健)
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报告发布 ▏吴晓林:超大城市风险防控的脆弱性与行政区划
2021年9月29日下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晓林教授在“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做了题为《超大城市风险防控的脆弱性与行政区划》的精彩发言。
文/吴晓林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晓林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超大城市的发展情况。目前,我国有7座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18%,但却贡献了全国32.9%的GDP,未来随着一些新兴特大城市的出现以及现有特大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特大城市占全国GDP比重的预期还将继续上升,甚至未来可能占到50%以上。但人口规模与城市风险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研究表明,在大城市中,随着人口规模增加100%,犯罪率会增加120%,一项在广州的研究表明,不论是侵财犯罪风险还是把暴力犯罪风险,皆是旧城区最大,核心区最小。既有研究基本都是以空间规划和人口规模的调整作为风险的系统变量,以疏解人口和进行空间隔离作为控制风险的手段。
吴教授认为,现有研究仍有缺口,因为并不能通过空间的界线划分就能很好很好地应对城市风险,行政区划只是影响风险防控的一个系统变量,真正影响风险防控的是附着于区划之上的“脆弱性”(反面就是韧性),但是,相关研究缺乏风险防控与空间脆弱性的关联分析。中国城市对风险的防控基础是属地化管理,我国的最高层法律和具体法规确立了每个层级政府主体的责任,要求把乡镇、街道(到了基层则把村、社区)都纳入到风险防控体系中来,各负其责,进行属地化管理。
吴晓林教授探索归纳出属地化管理的三类脆弱性。第一类是行政区与管辖权不统一的风险。在特大城市中,有些地方甚至分不清街道办的具体管辖范围,各种原因造成的插花地的管理和责任归属则更加难以界定。另一方面,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功能区,和行政区划是重叠关系,当出现问题时便难以问责,2013年青岛油管爆炸和2015年天津港大爆炸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第二类是风险跨区域“溢出扩散”,既有属地管理无法应对。城市的风险灾害不是孤立事件,往往是以灾害链的形式出现,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公共卫生管理,由于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单独靠一个行政区划来应对几乎不可能,我们对口支援和联动机制较好地缓解了这一点。第三类是区划规模太大,风险治理超载。在我国的特大城市中,建成区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数量超过一万,佛山的城市建成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承载的人口甚至超过六万,我国最大的街道办超过一百万人口,最大的小区达到五十多万人口,在此情形下,我国基层管理往往是一个管理人员对应一千人的社区服务,在具体的风险防控中承担了大量的职责。调研表明,目前社区在辖区内需要承担29项安全检查,但是社区缺乏对应的专业能力和行政手段。
针对属地管理在风险防控方面由物理特质和社会特质所带来的脆弱性,吴教授基于脆弱性的理论视角,提出了三区、三圈层韧性城市的路径。第一是在社区层面,基于人居安全需求推动安全场景营造,真正服务于人的需求。第二是在政区层面,基于人口密度和规模做好行政区划,避免中心城区或郊区过大,必要时推动行政区划从块状向扇形转变,以利于区划调整和优质资源向外扩散。第三是在跨区层面,基于安全风险的类型推动跨域治理,日常风险可以由行政区自行承担责任,例外风险就需要区域间的协同,诸如疫情这样的战略风险则需要跨区域协同。
(本文系嘉宾9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文稿整理:林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