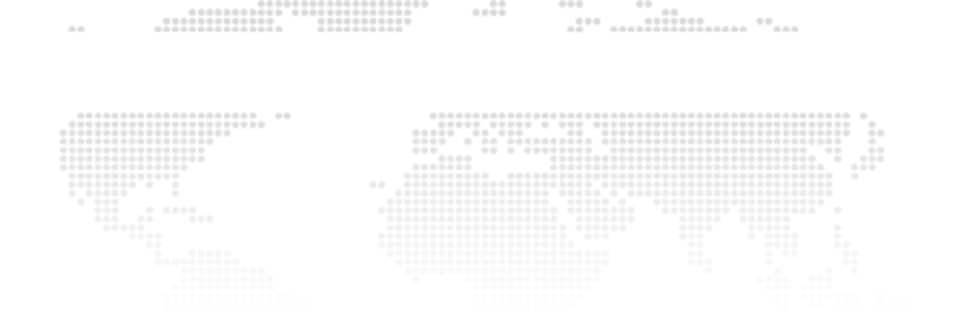《每日经济新闻》|叶裕民:为新市民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是市民化最大难点
编辑: 阅读量:加载中... 发布时间:2023-05-30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叶裕民表示,应该进一步用“可支付健康住房覆盖率”和“新市民与子女‘在一起’指数”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的考核指标。

“国家推进市民化的基本思路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轮驱动,评价标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镇化率的差距。从提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已经接近10年,我国两率差距不仅没有明显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我国市民化的难点到底在哪里?要不要改变思路?要不要创新考核办法?”
5月20日,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年会暨青年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叶裕民作了题为《我国市民化的难点与突破口》的主题演讲,谈及市民化最大的难点及考核机制的创新。
“所谓市民化,其实是一个让流动人口享受城市服务,并且在这成长融入城市的一个过程。从国家高质量发展而言,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也是他融入城市、享受城市发展成果。”她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她看来,我国市民化的基本思路是可行的,但是重点不够明确,需要创新考核办法,找到新的抓手,“比如,可支付健康住房覆盖率和流动人口与子女在一起指数可以替代两个一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如果超过95%就很好,给一个公平的起点,真正享受城市权利。”
最大难点是“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
“要明确市民化的本质内涵,是让新市民享受到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的城市权利,实现同城同权,户改只是手段。”叶裕民指出,从空间上看,超大城市是市民化的最大难点;从内容上看,当前用两率差(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值)作为市民化的抓手,没有充分反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市民化的贡献。
她进一步指出,从“十五”时期以来我国已经大幅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流动人口,在公园、公共交通等很多领域都没有障碍,但是很多超大、特大城市在一些排他性公共服务上并不能完全覆盖。
比如,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率较低。根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有流动人口子女儿童2719万,真正进入城市公办学校的仅占41.7%,数以千万计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在青少年成长期缺乏父母的保护和陪伴。
叶裕民根据多年对北京、广州、常州、深圳等地新市民的数千份问卷发现,新市民最需要的第一是子女入学,第二是健康住房,而子女教育问题又要依附于住房问题的解决,“正规社区都是多少常住人口配多少学位,但是城中村因为权属关系复杂,想要插进大量的人口或学校难度非常大”。
据她透露,大概有20%的流动人口通过自己的打拼逐渐走向可以购买商品房的状态,还有20%的人住在工厂、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最后剩下60%的人依靠租赁住房,其中绝大多数只能租赁价格较低的城中村的非正规住房。
这也能够从统计数据中得到印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60%住在城中村,其中住房贫困人口高达2800万。其中,七个超大城市住房贫困人口在87万到770万不等。这些流动人口的聚集区主要在超大城市外围形成的城中村,面积从几百到上千平方公里不等,构成超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的巨大难题。
“当前,没有一个城市有能力为如此巨大规模的住房贫困人口提供公共住房和集租房。”叶裕民表示,无论是从新市民需求来看,还是从国家现代化的需求来看,如何为新市民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也都成为市民化最大的难点。
把“住房”和“教育”作为新的考核指标
下一步应该如何进一步提升可支付健康住房的覆盖率?
“政府现在努力用公共住房和集租房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可支付健康住房,‘两条腿走路’。但是这个需求规模实在太大,短期内很难替代城中村提供的大规模存量住房。”叶裕民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她的长期跟踪调研,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建构城中村更新与新市民可支付健康住房的联动解决机制。
在过去城市发展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通常会把周边农地征收过来,但是村庄居民的建设及居住用地并没有及时征收,“这就造成了城市包围着村庄向外拓展,从而形成一个个城中村。”叶裕民指出,与此同时很多外围产业发展起来,彼时规划还没有对城中村进行限高、控制,所以居民就在宅基地上建了很多用于出租的房子。
这些房子客观上是非正规房地产市场另一种供需平衡的空间载体,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住房保障作用,“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和他们需求相匹配的栖息场所。”不过,它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进来,村庄又没有太多能力提供公共服务,比如子女入学问题,居住品质很低。
“我们要尊重这样一个历史逻辑,历史上城中村就是给流动人口提供了可支付非健康住房,那么我们现在通过城中村更新能不能继续为他们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叶裕民指出,应该对城中村开展系统的包容性更新,充分利用补偿给村民的合法住房面积,扣除其自住部分,将其出租部分规划设计为新市民需求相匹配的可支付健康住房,即成套住房。
以广州为例,根据她的测算,如果完成50%的城中村更新,广州新市民套房覆盖率即可达到97%到120%,基本实现新市民住有所居。比如,合法补偿面积是280平方米,可以100平方米自住,剩下180平米设计为6套30平方米的健康住房用于出租,“改造以后就是正规社区,执行市场租金,但因为供给量大,租赁住房的供求关系持续得以改善,直至达成新的供需平衡,租赁住房价格回归到均衡水平”。
在叶裕民看来,流动人口有了正规住房,政府就可以根据社区常住人口配套基础教育,这就解决了新市民最急难愁盼的教育和住房两大难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她表示,应该进一步用“可支付健康住房覆盖率”和“新市民与子女‘在一起’指数”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的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