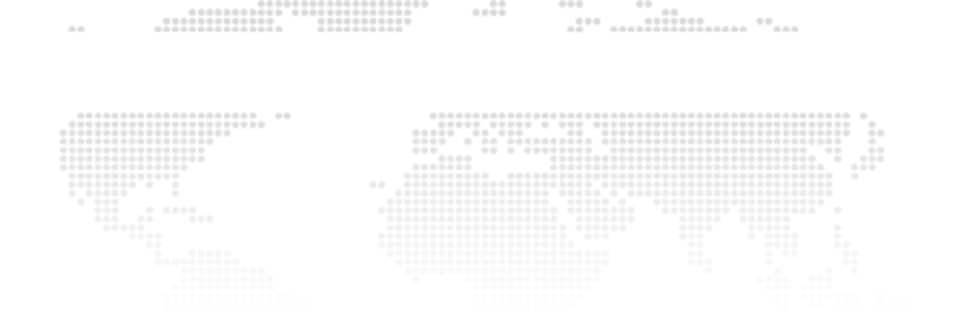专访人口专家张耀军:京沪常住人口微降治不了大城市病
编辑: 阅读量:加载中... 发布时间:2018-01-30
1月19日,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显示,2017年,京沪常住人口同时下降,为1978年后的首次。其中,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下降0.1%,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418.3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7万人。
人口的减少,伴随的是城市功能定位的调整和聚焦。北京自2014年提出“四个中心”定位,2018年1月24日,北京市代市长陈吉宁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优化提升“四个中心”功能作为首要工作,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大城市病;1月4日,上海市政府正式介绍新城市总规,点明上海市未来聚焦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建设的发展方向。
京沪城市定位的明确,伴随的是非城市定位功能的疏解和控制,人随产业走;而另一边,以省会城市为主的二线城市亦打起了“人才争夺战”。京沪常住人口下降是否已呈趋势?中国未来城市发展将会呈现何种格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张耀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常住人口下降不一定治得了大城市病。治疗大城市病,根本还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城市的服务、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
疏解非城市定位功能是主要原因
时代周报:本次京沪常住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庞江倩分析了四大原因,包括全国范围人口总量的低速增长,城镇化带来的特大城市人口流入下降,以及京沪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低出生率。你对此怎么看?
张耀军:就北京来说,常住人口下降还是与疏解非首都功能有关。疏解非首都功能不仅是疏解加工制造业等一般性产业,还包括医院、学校和非核心的行政事业单位。所以,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常住人口下降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二线城市例如西安、郑州、武汉等,在京沪疏解人口时,正用更大的力度吸引人才,呈现“一边在输,一边在引”的局面,尽管一边阻力很大,但另一边的引力也很大,会让一些有技术、懂管理的人才流入到吸引人才力度较大的城市。第三个原因是生活成本的提升。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整治群租住房,北京的生活成本将越来越高。第四个原因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中国父母注重孩子的学习和教育,为了调控人口总规模,五证齐全是孩子在北京上学的必要条件,这也会让一部分家长因为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而回到户籍所在地。
我不认为其他原因是此番京沪常住人口下降的重要原由,生育率可以算一个,但不是主要的。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人口一定是迁移增长,大部分的外地人口迁入才是最重要的,北京本地的出生率影响不大。
时代周报:201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出现197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1997年北京也出现了首次下降,但往后持续增加。就你看来。目前这种下降是不是一种暂时性现象?北京自2011年后,人口增速增量双下降,能否就此预测人口拐点?
张耀军:我认为目前这种下降是暂时的,同样以北京为例,是政府背后付出很大代价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结果,但是人往高处走,市场一定是让人口往就业好、收入高的地方迁移,虽然疏解成本高,但是在付出服务和劳动力的时候,相应费用也会提高即收益提高,在这种市场力量下,从长远来看,人口还是会增长。
但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省会城市如郑州、武汉、西安等城市的建设越来越好,医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那么京沪对人口的吸引力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大。在美国,每个城市的定位不一样,但收入、生活质量差不多,那么人们综合权衡时,如果城市间差距不大,就不会付出高昂成本迁移到另一个城市。京沪吸引人口能力那么强的原因就在于,其资源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未来如果省会城市乘势而上,提高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水平等,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拉近与京沪的差距,那么在吸引人口上,中国城市从差距明显走向均衡是有可能的。
但目前还很难预测京沪的人口拐点,无法预知何时常住人口的下降会呈趋势。这其中有很多变数,一是中国总人口规模的变化,再是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例如我刚提到的省会城市,这些城市什么时候能在人们的心理评估中与京沪的差距不大,很难预计。
常住人口减少不一定能治大城市病
时代周报:常住人口减少能否治疗大城市病?在京沪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服务行业其实亟须配套升级,但疏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对城市发展产生怎样影响?或者说,人口吸引力能置换人才吸引力吗?
张耀军:两地发展这么快,其实是利用了全国的人口红利,高素质的年轻人流到京沪,稀释了当地的老龄化水平,缓解了京沪的老龄化进程。但一个城市有2000多万人,通过减少两万人左右,是不能治疗大城市病的,没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大城市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就已经不再属于大城市了,也无需在乎城市功能等,问题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常住人口下降不一定治得了大城市病。治疗大城市病,根本还在于千方百计提高城市的服务、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比如现在北京完善地铁等交通服务设施,通过类似基础设施的改善,服务水平的提升,多管齐下,才能整治大城市病。我一直认为,一个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堵车等现象,就像人吃多了会胖,其实都是正常的,在可控的范围内都是可以的。
一个城市的发展,应该让生活更美好。北京市政府之前也强调过,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时,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如果还能使生活水平更提高就更好了。
城市最根本的属性还是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城市生活越来越方便,才是城市发展的方向。
时代周报:京沪常住人口下降是否产生了外溢,比如人口往周边城市或强二线城市迁移?如果是,这会否进而引发城市格局变化,在国家倡导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产生新的城市群?
张耀军:是会引发城市格局变化。中国目前的城市框架是拉开了,但内涵的城市化道路还走得远远不到位,即城市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城市框架下的人口密度、人口居住的舒适程度、便捷程度、城市建设的水平等还没有达到相应水平。但是城市框架拉开了,未来第一步会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促进这些地区的建设。
此外,国内二线城市的总体综合实力,包括医疗、教育水平等,跟一线城市比还是有些差距,但是“一花独开不是春”,以省会城市为主的二线城市一定会吸纳、消解大量人口,这是大势所趋,中国人口基数太大,14亿,只靠几个一线城市是不可能的。
二线城市要拉近与一线城市的差距,中国城市要慢慢走向均衡,所以北京和上海在疏解与定位不相符的城市功能时,恰恰是一些以省会城市为主的二线城市争抢创新人才的黄金时期,借势而上既减少了京沪人口流入,也能慢慢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时代周报:目前深圳和广州的常住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预测仍在增加。京沪和广深不同程度的人口调控,是否关系到城市的不同定位?
张耀军:肯定是,北京聚焦首都功能,上海是金融中心等,广州和深圳也一样,城市的管理和调整一定要与定位相一致。
目前,广州和深圳就如双子星座,广州是广东省省会,但其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比不上深圳,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广州不必迷茫,国际上的很多政治中心未必是经济中心,这很正常,是城市分工当中应该走的道路,每个城市都应该突出自己的主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