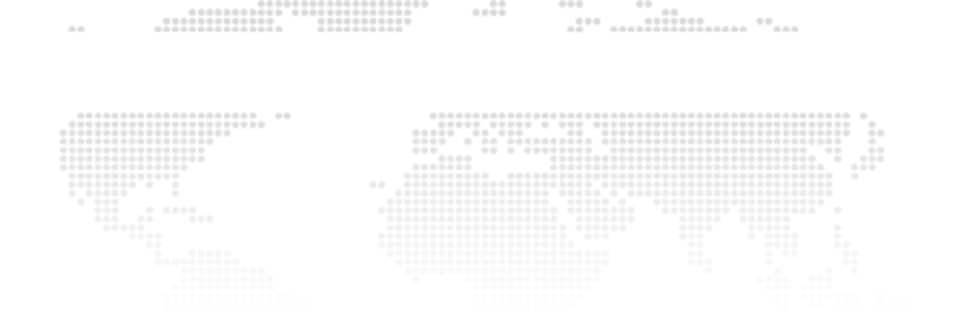第七届首都治理论坛丨王亚华:激活超大城市治理的社会机制——兼评“接诉即办”案例
编辑: 阅读量:加载中... 发布时间:2021-04-04
2021年3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亚华教授在“第七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的新理念”上做了题为“激活超大城市治理的社会机制——兼评‘接诉即办’案例”的精彩演讲,从农村研究的独特视角来审视城市治理,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探讨有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治理路径。
从农村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社会治理面临很大张力。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向市场化转型,现代社会面临的公共事务问题越来越繁重,政府不断向市场和社会分权,但是分权的效益更多体现在经济建设领域,公共治理领域却存在着广泛的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市场和社会未能很好地分担政府的公共治理职能,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政府的依赖,比如脱贫攻坚、河流治理、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制度设计更加依赖政府。反观当代中国城市治理,呈现出同样的制度演变趋势。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在于越来越依赖自上而下的党政力量,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作用有限,且二者没有很好融合,使得农村基层治理具有强烈的党政主导色彩。一些村组织表现为乡镇政权的自然延伸或办事处的角色,广大村民处于被动参与的地位,面临广泛的合作困境。此外,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很多村社财政困难,自我造血能力差,基层服务组织人力资源短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低下。城市治理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随着党政力量统合不断强化,基层治理中“干部干、群众看”现象普遍存在。而政府由于负担重,规模越来越大,涉及专业领域非常多,干预领域也越来越广,加之财政的约束,基层政府职能面临很大的考验。
城市和农村表现出相似特点的原因在于它们面临相似的体制架构。在我国基层治理体系设计上,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农村村委会和城市居委会理论上都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现实中,由于自治单元过大,容纳人口过多,基层自治治理能力不足,往往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解决大量基层事务。尽管城市享有拥有多种生产要素积聚的优势,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体制架构伴随的制度问题。农村治理存在三个方面的基本制度问题:一是规则供给方面过于依赖于外部供给,导致农村基层自主性受到了抑制,规则适用性和规则一致性的问题较为突出;二是规则执行方面依赖于外部监督和正式惩罚,农村固有的内部监督和非正式制度优势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反而较小;三是规则保障方面过于依赖自上而下的干预,这是基层治理很多问题的制度根源。城市治理相对于农村治理而言,更加依赖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正式制度与外部监督,更需要高强度的资源投入和支撑保障,这些特性进一步强化了对政府、正式规则和外部监督的依赖,因而上述三个基本制度问题在城市治理中同样广泛存在、甚至更为突出。
利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层次嵌套制度分析”发现,中国在宪制选择规则和集体选择规则层面的制度建构比较强健,但由于基层自治不够发达,导致大量操作层次的规则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包括:(1)规则缺失问题,大量新兴公共事务缺少规则;(2)规则不适问题,现有规则不适用于日益广泛的基层治理问题;(3)规则执行问题,已经存在的规则不能很好地执行,制度漠视和不完全执法的问题比较严重。上述问题本质上是基层运行中的制度设计、制度变迁和制度执行,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对制度建设的巨大需求。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上述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应,较为典型的举措包括:(1)改革基层组织,例如大量农村地区推行自治单元下沉,设置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等新型社会组织;(2)加强规则供给,例如完善法治、加强德治、推进自治,更加重视乡规民约;(3)规范基层权力,例如浙江宁海推行小微权力法定化,发动民众监督基层组织、强化社会监督和上级监督;(4)打造沟通平台,例如上海“一网通办”、浙江的象山“村民说事”、嘉兴“睦邻客厅”等创新举措;(5)应用数字技术,例如“乡村钉钉”、“掌上乡村APP”、“浙里办”等典型案例。这些响应的意义在于通过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听取民意,吸纳民智,汇聚民力,激活基层运行中的社会机制,贯通上下力量,建立多元共治新机制。
如果运用上述分析视角和理论逻辑来分析北京市“接诉即办”案例,可以深化对超大城市治理机制的认识。北京市的“接诉即办”改革,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在于有效地解决了三个基本制度问题:在规则供给方面,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街道为基点,打破了“条块”分割壁垒,推动跨层级协调,跨部门联动;在规则执行方面,建立了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三率”评分、四级响应以及每月绩效考核为核心的实施机制;在规则保障方面,广泛应用大数据技术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规范。当然,由于“接诉即办”实施时间不长,还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1)社会治理更加依赖政府的力量,对社会机制产生“挤出效应”;(2)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较为简单化,技术运用的线性思维尚未适应复杂社会治理;(3)考核体系中的“条”“块”间的考核力度与任务压力不对等;(4)体系运行中自下而上的评价和反馈机制的科学性有待提高。此外,“接诉即办”的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
基于对中国城乡治理变迁的观察,以及对北京市“接诉即办”案例的分析,对于超大城市治理改革有以下思考和建议:(1)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特别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共同参与的议事沟通和协同治理机制;(2)激活城市基层自治,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各种机制,积极发挥群团组织和微社会组织的作用;(3)保障基层组织的规范化运行,推进基层小微权力的法定化和透明化,建立多层次监督机制,保障基层权力规范有序运行;(4)发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平台,畅通干群沟通和群众参与通道,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城市社会治理能力。
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格局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三者的互补互动。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力量发育不足,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在社会治理中广泛吸纳民众参与,充分运用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国超大城市的治理,尤其需要重视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多种途径激活社会机制,让社会机制在城市治理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总体来看,中国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牢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充分运用数字治理的力量,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的治理新格局。